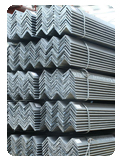父親的書房里,懸著一幅他手書的條幅:“今人不見古時月,今月曾經照古人。”每當墨香混著舊紙的氣息在午后彌漫時,我便覺得,那不只是十四字的詩句,而是一扇正被緩緩推開的、通往千年之前的門。
起初,門的那邊是模糊的光影。老師教我“白毛浮綠水,紅掌撥清波”,我只見得幾只肥碩的鵝;背誦“床前明月光”,也只當是灑在地板上的幾縷清輝。它們像被精心裝裱的標本,美則美矣,卻失了體溫。直到那個秋天。風里第一次透出涼意,我獨自走在郊外,為一場失敗的比賽而郁郁難平,腳下一滑,險些跌倒,低頭卻見一層薄霜,像上天漫不經心撒下的鹽,正覆蓋在衰敗的草葉上。剎那間,一句幾乎被遺忘的詩掙脫了課本的囚籠,帶著全部的重量與寒意,撞入心扉:“蒹葭蒼蒼,白露為霜。”我猛地站定。那不再是被反復注解的文本,而是一千年前,同樣一個微涼的清晨,另一雙眼睛所見的全部真實。他腳下的霜,是否也是這般帶著欲言又止的凜冽?他眼前的蘆葦,是否也在風中傳遞著無言的蕭瑟?那個“所謂伊人”,那個求之不得、輾轉反側的目標,于我,不就是那份渴望卻失落的榮光么?原來,我們共享著同一種生命的戰(zhàn)栗。那扇門,在那一刻,被一種跨越千年的共情轟然推開。自那以后,古詩詞于我,便成了無數(shù)面映照心靈的古老銅鏡。
我在“行到水窮處,坐看云起時”的鏡前,照見自己的焦慮與局促,繼而學會在困厄中尋一份坦然的轉身。在太白那面狂傲不羈的鏡中,“仰天大笑出門去,我輩豈是蓬蒿人”,我窺見自己內心深處同樣不肯被馴服的、屬于少年的火焰。而在老杜那面破碎的鏡子——“國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里,我觸摸到一種超越個人悲歡的、對蒼生社稷的深沉悲憫。這些鏡子,由語言鍛造,被時間打磨。它們不是冰冷的文物,而是依然溫熱的、能與當代生命發(fā)生劇烈化學反應的存在。我們讀詩,原來不只是鑒賞古老的修辭,而是在無數(shù)面鏡中,辨認出那個似曾相識的、屬于“人”的自我。
又是一個夜晚,我讀完“十年生死兩茫茫”,掩卷望向窗外。城市燈火璀璨,早已不是東坡筆下那個“明月夜,短松岡”的孤寂世界。但我知道,那輪宋時的月,正無聲穿越我的窗,如同它曾經穿越朱閣,低照綺戶。我在這光中站立,如同一面新磨的鏡,與無數(shù)面古老的鏡,靜靜地,交相輝映。